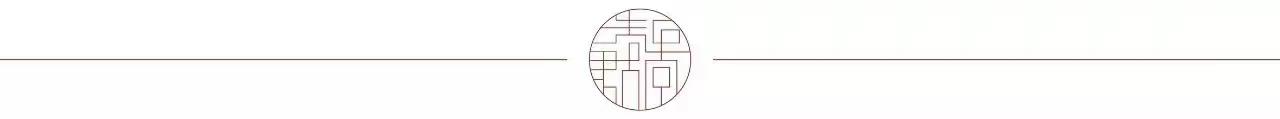茶山游

我是一个不懂茶的人,至少在我站到茶山的土地上之前,我对茶山的了解,近乎一无所知。庆幸的是,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当我抬起我的相机去取舍我的所见,当我迈开我的脚步去丈量我的所行,当我用心去听每一个茶山上的故事的时候,即使一无所知,依然被打动沉醉。茶山上的人事太多,三天的时间太短,三个人的故事,献给大家一篇茶山变形记。

(莽莽茶山里藏着多少奇人与故事)
第一个人是雷平阳老师,诗人,云南人,《普洱茶记》、《八山记》的作者。
记忆里关于普洱茶的印象,都来源于许多直观的图片,坐而论茶,饮而优雅。第一次听到不一样的普洱茶印象,是在智默国际茶友会的研讨会上,雷老师是第一个发言的老师。40分钟的发言里,“鬼神”二字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雷老师的普洱茶神启,是来自于一场爱伲人的葬礼,同样刷新了我的认知:在爱伲人的葬礼上,对于死者的祭品,有且只有一种,就是茶叶,普洱茶,悼念的人将茶叶放置在死者的七窍各处,追念结束的句点,祝福下一个开始,完成一个神圣的过程。联结现世与鬼神的东西,是茶叶,普洱茶。隐约间,普洱茶的身份,开始从那些由消费主义建构起来的浮夸里剥离开来,渐渐接近它最本质的模样。

(雷平阳老师在智默国际茶友会上真诚发言)
当我在倚邦彝族香堂人家里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雷平阳老师所说的鬼神:沉默的老者端坐在噼啪的火塘边,烟尘在昏暗的光里折射出了诡异的形状,神秘主义的气息在空气里蔓延。煮水的大锅上附着着厚厚的黑垢,在山上已经通电的日子里,家家户户的柴房都是储备充分的,火塘下面厚厚的灰可以证明火塘从未间断过使用,关于山上煮茶的习惯是早有考证的,于是我在回想,当原始的原住民在火塘上的沸水里放入第一片茶叶的时候,应当是普洱茶神圣的开端。

(香堂人家里,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气息)
那次与香堂人火塘的亲密接触,应该是山间鬼神对我的神启,由此拉开了序幕,让我真正能以一种不同的感觉行走在这片山林里。在《八山记》的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一幅流着血泪和茶汁的茶山画卷。”在回来记述感慨的今日,我想,如果我没有恰好听到雷平阳老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如果我没有恰好看过《八山记》,我是否能有别样的感慨?答案应该是不能,雷平阳在《八山记》的自序里写道:“我着迷于普洱茶,乃是倾心于它那无出其右的品质,孕育了世界茶文化史而又几千年隐身于滇土的操守,以及它与茶山民族之间神鬼莫测的生死关系。所以,我弯下了腰,尽可能地紧贴一座座茶山。”每年上茶山的人甚众,但我所见耳听的个别,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昂着财富的头颅来到这片树叶能变金叶子的山里淘金的。当站着的诸位,以现代文明的优越感来俯视这片群山的时候,是否又知道,茶山的鬼神,需要弯下腰,乃至趴在地面上,才能依稀听见神秘的呼唤呢?

(火塘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起源及聚集地)
第二个人,是曹当斋,或者说死掉的曹当斋,曹姓贵族,勐腊县倚邦土千总,自清雍正年间曹家世袭管辖倚邦、革登、蛮砖、莽枝茶山,负责贡茶采办。

(曹当斋墓前的麒麟石刻,散落在丛林里)
对普洱茶历史稍感兴趣的人,应该或多或少听过倚邦和曼松贡茶的故事,听说过古六大茶山的辉煌。在上倚邦山之前,关于倚邦茶的贵族形象,已经深深扎根进了我的心里,只是,当我站在倚邦山上最富传奇色彩,深受倚邦人民爱戴的曹当斋的墓前,历史似乎向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映入眼前的是坍圮不堪,近乎生长在丛林里的遗址,是的,我用了生长二字。石雕、台阶、墓碑凌乱的散落在丛林里,用一种近乎荒唐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格格不入,又浑然一体。当我俯下身来观看和拍摄遗址的时候,盘结的树根,角落里的蛛网,以及空荡的墓穴,诉说着这里长久而彻底的荒颓,然而同样是比肩而邻的石碑,精致的麒麟石刻,瘫倒在地上石匾上依稀可见的“荣封俱庆”四个大字,又时刻提醒着,这里曾经是一个贵族家族荣耀与身份的象征,加剧着我脑海里的荒唐。

(刻有“荣封俱庆”的石匾)
让我们用史料来梳理一下倚邦的故事吧,
明成化年间(约1470年左右),曼松茶因色香味俱全且冲泡不倒被定为朝廷贡茶,明王朝任命倚邦叶氏为土司负责贡茶加工生产,倚邦初次登上历史舞台。
明隆庆四年(1570年)六大茶山和整董和为茶山版纳,倚邦成为六大茶山政治中心和行政主管地。
清雍正七年(1729年),倚邦土弁曹当斋因在改土归流中协助清军平乱有功授封倚邦土千总,曹氏家族世袭管理倚邦、革登、蛮砖、莽枝近二百年,倚邦作为六山中心进入昌盛时期。
1937年,法国人在越南阻挠云南茶出口,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倚邦茶商农逐渐迁移歇业,热闹喧腾了二百多年的倚邦陷入冷寂萧条。
1942年,攸乐人联络瑶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举行抗暴起义,战事一直打到小黑江对面的曼林、牛滚塘、秧林、倚邦等地,倚邦老街在一场持续三天三夜的大火里化为灰烬,衰落至今。

(如今的倚邦老街,过去的痕迹已经快消失殆尽)
213年,倚邦的辉煌停留在了这个数字。顺着村民正在新建的房子施工的尘土走进倚邦老街的时候,我试着去想象文献里那个无比辉煌的倚邦,那个数十万人入山做茶,石屏会馆四川会馆林立,倚邦茶远销欧洲印度的年代,然而寻得的,大抵只是几块夹在红砖里的浮雕,几片瘫倒在路边的石条。只是那条叉出去青石板路上的青苔,和那口大榕树下的古井,依稀在提醒着,这里曾经有过辉煌。石板路上那些一米见方的青石究竟是不是曹当斋派人用大象驮上如今路途甚是遥远的倚邦古街已然成了未解之谜。那口倚邦古井在当时是贵族人取水之地平民不得取用的传说也很快要从山里老人的口中永远沉默下去了。两百年的兴衰,转瞬烟云,令人唏嘘。

(倚邦的老水井,倚邦在当地语里的意思为“有水有茶”的地方)
75年,这是曹当斋墓生长在倚邦山里的日子,当倚邦的辉煌在火光里黯然逝去,曹家的后代也终于失去了保卫自己荣耀的能力。于是历史与自然在这片山林里静静和解,默默守卫,时间与自然遮掩了历史沧桑和丑陋的疤痕,然而倚邦的荣耀与辉煌,却无处安放,至少,不是在倚邦老街树立起的钢筋混凝土里。

(布满青苔的青石老路,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这些石头是如何被运上山的)
第三个人,给老金先生。金容纹,韩国人,光山金姓,智默堂创始人,十年普洱茶制茶人。
毫不夸张的说,茶山是老金先生第二春。平日里在昆明智默堂总部的时候,老金先生衣服的颜色,多是灰色黑色居多,即使是智默国际茶友会上,老金先生也是选了一身黑色的呢子大衣。然而在版纳告庄见到老金先生的第一眼,仿佛年轻了十岁:红色的格子衬,被山路上的风吹得翘起的头发。无不传递了一个信号,这里,是我最舒畅的地方。

(凌晨六点半,老金先生在倚邦初制所)
关于老金先生的传奇故事,我们应该是听了最多遍的:自然主义者、禅宗弟子、富家子弟外国人到云南做普洱茶,只是这一次上山的路上,我私自决定给老金先生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古六大茶山车神。凌晨五点在狭窄的土渣山路上全程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上山,事后在山上的时候,老金先生轻描淡写的叙述了车神的自信:这条上倚邦的路,我开过不下二百遍。一年上山二十遍,十年两百遍,这是属于金荣纹的仅仅一座茶山的数字;60万,一车石头拉上山比肉贵,这是老金先生的新倚邦初制所投入的数字,而当我们站在新倚邦初制所里的时候,有的只是一栋孤独的从易武搬过来的老房子,以及倚邦山里沐浴在日出里一片烂漫的山花。——“倚邦山上的日出与云雾是最漂亮的。“这是老金先生解释上山路开这么快的第二个原因。

(山花烂漫的倚邦山谷里的日出美到让人窒息)
在无数次的交谈里,老金先生都从来不掩饰倚邦茶便是他的最爱,当看着新倚邦初制所里那栋孤独的房子和漫山遍野的山花的时候,我想我是理解的,在看日出的时候,老金先生带着我们憧憬了他对新倚邦初制所未来的规划:智默人的六星级山间居所,一次真正在茶山上的智默茶友会,言语间满是孩子般的骄傲和迫不及待。老金先生对倚邦的爱应该是纯粹的,也曾说过澜沧江沿岸的茶山他都走过,唯独到了倚邦的时候,心里的声音告诉他,或许他的前世今生,就是这里的人了。前世今生我们总是不得而知的,但老金先生在倚邦初制所上的返老还童,我觉得是不骗人的。

(这栋老房子,是老金先生在易武拆房子时候抢下来一砖一瓦的拉到这里的)
雷平阳老师在智默国际茶友会研讨会发言的时候说,在这个普洱茶纷繁错杂的年代里,是需要更多大师进山做茶的,需要一些近乎神灵一样的精神去敬畏和提升普洱茶。老金先生不喜欢被人称为大师,但进山这件事,一做就是十年,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这个茶山是会吃人的,不仅吃人,还吃钱,老金先生在边上,眯着眼笑笑,不说话。

(这片看起来依旧是一片荒地的新初制所已经吃了老金先生60万)
一座茶山,能做什么?能把树叶变成钱,能把人变成鬼神,能把历史长成丛林,能吃了一个茶人的一辈子,只是真正走进茶山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以山观人,以山观己,回来的日子,再端起那一杯茶的时候,我才开始一遍遍的审视,审视茶山上的人,茶山上的事,审视自己。我想,我应该是爱上茶山了,当我贴近那些百年生长在那里的茶树拍摄的时候,隔着镜头都能体会那原始而强壮的生命力;当我用手抚摸倚邦老街的青石墙的时候,二百年的兴衰荣辱在我眼前飞速略过;当我坐在老金先生边上与他吹着茶山上同一片山风的时候,我能依稀触碰到这个男人纯粹而坚毅的茶心。

(制茶这条路很长很苦,老金先生会一直走下去,智默人同样如此)
茶山上的变形记,还在发生,还在继续,惟愿我的故事,我的图片,能帮您揭开茶山神秘的面纱,在那一碗杯中的茶里,平添几分滋味,如是,唯爱茶人之愿也。